台灣高教體制的問題:高中、大學、研究所
儒家思想深深影響著華人的社會,
但是到大學以後,就完全不是這一回事了?一個大學聯招後,
當然會有人抱持著反對的意見,
研究所,又進入了另一個環境,除了修課外,
因此夏老師在文中所提及的高教體制的乖離現象,
名次代表著競爭力,急功才能反應社會的現狀,
在當然的台灣教育體制中,很難去跳脫上述所談到的。
這樣的批判是合理的嗎?我並不認為行動劇說明了高等教育的荒謬,
參考來源:
但是到大學以後,就完全不是這一回事了?一個大學聯招後,
當然會有人抱持著反對的意見,
研究所,又進入了另一個環境,除了修課外,
因此夏老師在文中所提及的高教體制的乖離現象,
名次代表著競爭力,急功才能反應社會的現狀,
在當然的台灣教育體制中,很難去跳脫上述所談到的。
這樣的批判是合理的嗎?我並不認為行動劇說明了高等教育的荒謬,
參考來源:
"當今高等教育的現場,我們正在上下共謀地演出一場〈國王的新衣〉荒誕劇碼:教育部、國科會,透過層層關卡、考評、獎懲機制,已使得大學教師忙於生產無關現實與宏旨,卻有「點數」的期刊論文(最好是英文);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困惑,早成了汲汲營營「向上爬升」的老師們眼中急於踢除的絆腳石;各大學之間與教師之間,不僅排資論輩,更是火速的等級畫分,形成高教體制中的階級社會;在獨尊國立菁英大學與理工醫的邏輯裡,人文、社會科學以及私立學校,只能當個自悲自憐的賠錢貨;對體制不滿的老師為數雖眾,卻是噤聲不語,甚或急於鑽營…。 高教體制的光怪陸離現象早已不是新鮮事,大學教師的抱怨聲,早已瀰漫在所有大專院校的上空。然而,絕大多數的大學教師卻是敢怒不敢言,心裡即便百般不屑,仍繼續玩著向英美投降、力求能快速集得點數以攀爬學術階梯的遊戲。 在這個體制裡的大學生,從老師們的身教到底學到了什麼?究竟是追求真理、公義,亦或是虛偽、攀附權貴、製造與鞏固階級社會?在我們批評年輕學子沒有社會意識、急功近利時,是否曾反省:下一代的價值與行為,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教育成果?"
- 觀念平台-高教體制演出〈國王的新衣〉荒誕劇|言論新聞|中時電子報 (在「Google 網頁註解」中檢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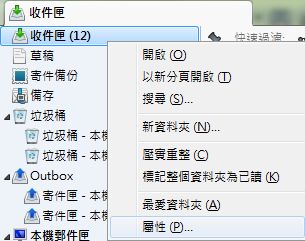
留言
張貼留言
,,